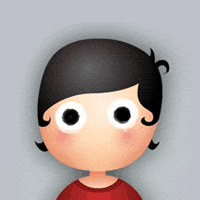草根叙事 II 闵雅君:回归,我迷人的琴笛
作者简介:
闵雅君:湖南省湘阴县高中语文教师,高级职称。工作之余以文自娱,身体欠佳以诗保健。有作品发表于《湖南工人报》、《湖南教育报》、《广州日报》和《星星》诗刊及地市级报刊。近一年多来,有十多篇散文和100多首诗在《草根叙事》等几种知名电子媒体上传播。
回归,我迷人的琴笛
闵雅君(湖南 湘阴)
我又开始吹奏放下二十多年的笛子和口琴了。
年轻时,在夏天月光下,在湘江边,轻轻吹一支竹笛,吹《我爱北京天安门》,给对岸的心上人听。那条河,好宽。涨了大水。我这边,乌龙塔只剩了半个宝塔尖;那边,无际的柳林杳无踪迹。只剩黑水星光。
但,我的笛声被风送过去了。我是把一颗心往对岸吹。我是在乌龙渡口见了一眼穿红灯芯绒的她,我就把那支曾为一中同学、后来省花鼓剧院的名旦谢小君伴奏过的那支梆笛拿出来吹了。好多人听了,心神驰骋,豪情激荡,夜半不眠,下田割禾,扯秧,晒牛(催牛耕田)。
性格开朗的她,第二天一早过了河,到了乌龙塔边我教书的那所中学,送来一窝鸭崽子,问:“你笛子里的天安门比喻我吗?是的,就把这一窝仔仔喂大,喂大了我们就……”
我怀着西窗剪红烛的梦想,将鸭崽圈在山墈边,抛五谷杂粮,喂虫子蚂蚁。她每周送一袋鲜谷过来,逗逗鸭子,帮我洗洗衣被……一个学期过去,那一窝小鸭崽子的脚趾长成了脚板,绒毛换成了粗毛,尖嘴换成了扁嘴,唧唧喳喳的昵喃换成嘎嘎的歌唱。分出了公母学会了追逐打闹。她也说:“过了年就……"
鸭子口琴笛子妻子送回了家,一个安在鹤龙湖边三代的家。那时,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
到了第二年开春,每到早晨打开笼子门,满禾场麻白色的翅膀扑啦啪啦,满屋场的嘎嘎欢叫,满眼的淡红色扁嘴向天张开,闹翻了天。几分钟后,扑啦扑啦扑到老土砖房子边的池塘里,惊得满塘小游鱼乱蹿,小米虾蹦出水面。一会儿,麻鸭们就上得岸来,挺着鼓鼓的大肚子,一字排开在塘边绿茵茵的霸粳草上,用淡红色的扁嘴,搓搽湿漉漉的羽毛。太阳升起来,它们头藏在翅膀上,香香的睡着了……
老爸弓腰翘股,在鸭窝里掏了半天,就有半脸盆鸭蛋吃力地端进了厨房,娘也从菜园蛇着腰,提满篮子活淡新鲜的萝卜白菜大蒜葱到蜿蜒曲折绿赛港的跳扳上洗去了。新婚妻子------现在的老伴带着两个月肚子里的佳宝宝下地去了。我洗了漱了,吹了一阵子口琴:《游击队之歌》,娘端来一瓦碗鸭蛋面,我索索索一阵子美美吞下,肚子胀得鼓鼓的好像塘边被老爸喂饱的鸭子。然后,骑着娘喂了一年猪给我买的凤凰牌自行车,压着窄窄的塘干去濠河八中赶早班去,惊得熟睡的鸭子们扑通扑通滚到池塘。
五月,小佳佳出世了。妻子考取民办教师了,我又考到师大进修了。我一生的修为之福仿佛在青春的边场一夜降临。
我们离开了茅草屋、鸭笼、菜园、池塘、绿赛港;我们离开了那群给我们下蛋,给我们舞蹈和歌唱的音乐家们。我就这样把我的老父老母丢在那个屋场上,连同那竹笛和口琴,一走了之。后来只是偶尔一小家子回去看看。渐渐地,那群音乐家一个个的减少,池塘里渐渐地起了浮萍,到年底鸭笼子空了,茅屋为冬风所破了,国防科大的讲师妹妹把父母接去过城市生活了。我的年轻时代的那曲短短的田园牧歌,结-----束------了---------
那是该结束的生活,还是应该放下所有续写的传奇?在那田园牧歌里,我收获了温暖终身的情爱。我用我的情和血,怀孕了我的血脉。我作为父母的满崽,在那茅草屋,有永远享用不尽的娇宠。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究竟要到那里去?是什么让我不假思索的远离?我连半个答案都没有得到就离开了。
我离开后的二十多年,鸭子们的翅膀老是扑打我的梦,那已经变成了两个叔叔坟场的老屋场,让我已经再也怕敢去依恋它了。
我的两个叔叔分别先我父母而去。那老屋场已没有父母安寝之所了。而今,父母下葬在湘阴城边的公墓,其魄离我很近,但其魂离我很远。要是两老安寝在原所,我和妻子、大佳佳,和我的老兄老姊妹,可以想什么时候回老屋场都可以。那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一定是:父母的墓边,池塘永伴,蔬菜青青,鸭子们生生不息歌舞升平在两老的坟头前。这是父母用一生创作的田园牧歌,他们多么想要享用这人世的弦歌千秋万代而不绝哦。
哦,好在公墓这边,荒野也城市化,公路盘绕,工厂热火朝天,世界大企业“远大”也落户在两老仙寝身边。父亲在世是朝闻道夕死可也之人;母亲有文化爱时髦,在世时,最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大城市老太太模样。如果两老在天有灵,他们会为阳世的繁华目迷五色,极视听之娱吧!果真如此,我心可安矣。
:我又开始吹笛子口琴了。那早已被我遗忘的我的青春记忆,母亲一直保存着。她离世于鹤龙湖畔的我老哥家。我们在为她抹敛时,从她的枕头下发现了它们。握着带有娘的体温的这两样东西,我的心好像被火灼烧。
现在,我的心回归自然了,女儿大了,嫁了。我也成了我当年的父母了。我住所前有五亩桑树林,四季闻鸟语;我的阳台,我伺候的一群小鹦鹉,俨然当年那群麻鸭;我楼下的吴娭毑李嗲嗲养了一群群鸡和鸭,老年痴呆了的退休老师陈德顺先生,朝夕相搀的陈教授夫妇,他们养了两只老黑鸡和一只小豹子狗儿,鸡狗同欢亲如一家,给几位老人生蛋献殷勤,好玩极了!我的眼前我的身边又开始演绎一曲新版的城市田园牧歌了。这该是一个多么神奇又何其富有戏剧性的收尾!
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无法回答的哲学命题,在我精神四季的轮回中,已经有了最佳答案。
我又开始吹奏《我爱北京天安门》,吹奏《游击队之歌》。我不再在回忆中感伤,只在晨光夕照中,任一缕风把我消瘦。
我怀恋往昔,我向往我那永无止境的地平线;我感激上帝,池塘,苍天!